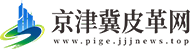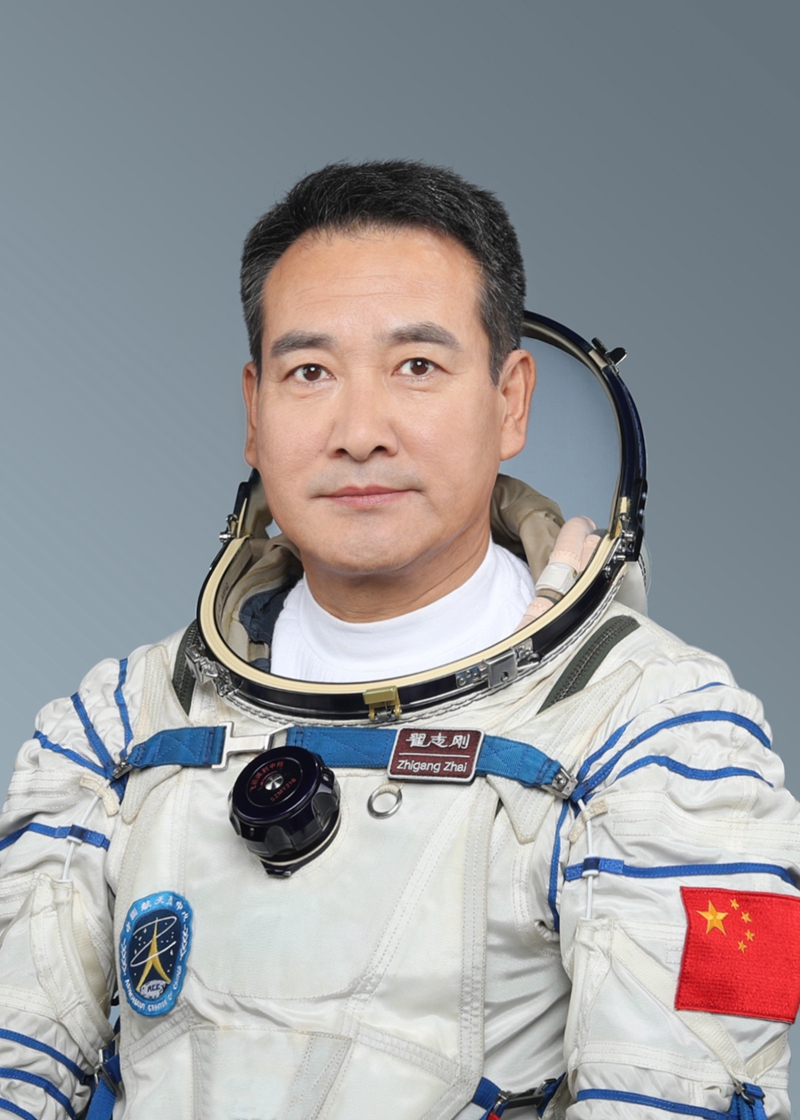作者|刘娟
写在前面的话:父亲已过90岁生日,有了闲暇的时间,经常回忆他童年的一些往事。我跟小妹不满足只做他的倾听者,希望父亲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亲人们都知道。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故事。
避难野坡1934年2月,我出生在山东潍县东郊梨园村一个农民家庭。家里有一亩多地,父亲是一个细木匠,常年在青岛铁山路一家名叫“德顺和木工厂”打工。他不仅能做一手好木匠活,还能在家具上雕龙刻花。母亲和我留守在潍县梨园老家,靠父亲做木匠的微薄收入补贴生活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1938年7月的一天,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:“日本鬼子来了!老幼妇女快藏起来!青壮年快拿起"家伙’准备着!”
隔墙东邻刘登皆手里拿着土炮,紧张地挨门通知。于是母亲匆忙收拾了几件衣物,领着我奔向东门。母亲是裹了小脚的,无论怎么着急也跑不快。途经南墓田刘一高的小铺子,她突然停下了,急急忙忙从小铺后窗给我买了三个高密大西枣(沾着芝麻的大糖圆)。当领我跑到三官庙东南坡一片高粱地时,母亲已经满头大汗,汗水湿透了她身上的衣服。她不顾自己,先用未湿的衣角给我擦头上的汗水。
七月的高粱叶子似刀片,刮擦着母亲的脸。我当时四岁多,身材低矮,高粱底叶稀疏枯萎,并不觉着刮拉。看到母亲脸上的道道小伤口,我问母亲疼不疼,她说不疼。直到下午,未听到村里的喧闹和枪声,感觉很平静了,我们才走出高粱地回到家中。这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避难。
漂泊青岛这年,母亲为了我的安全,找到将要去青岛办事的街里侄子五月,托他顺便领我去青岛找我父亲。
好久没有见到父亲,真想他。当我见到父亲时,别提多高兴了。到了晚上,父亲的工友们都下班了,唯有父亲还不离开工棚。我就拉父亲说:“大,咱也快回家吧。”父亲说:“咱这里哪有个家啊,这就是家。”
他一面说着一面收拾木匠案子上的木工工具,拿把笤帚扫掉案子上的木屑和刨花等杂物,伸展开铺盖卷儿,对我说:“咱爷俩就在这上边睡觉不是很好吗?”结果夜间我还滚落在地上,幸好孩小体轻未受伤害。
此景此情也深深地刺痛了父亲的心,他想方设法去寻找租房。住在聊城路润德里的我的叔伯大姨妈庄潘氏,给我们选了西岭最西面、靠海边的一个大杂院,大院里有铁匠炉、豆腐房小作坊,还有道士装束的人家等五六户人家,院内居民多数衣着褴褛,鞋帽不整。在这个院子居住的潍县上虞河老乡—-铁匠炉的一位老人和儿子,把一间半耳屋子(棚厦子)倒出来,租给了我们。租好房子,父亲就将我母亲接到了青岛,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
这个大杂院,地处海边一处南高北低的瞪眼沙石坡上。所租借的小厦子随地势而建,稍有找平。亲友找来了四条腿的两条长条凳,上面加上五页床板,搭成一张简易床铺。每天清晨起床,一家人身上都片片红包,奇痒难耐。褥子上满是点点血迹,原来就是床板裂缝中的臭虫饱吸我们的血后,被我们身体给压死的结果。父亲去铁山路上班,要经过大牛房胡同,横跨青岛火车站铁路天桥,越过费县路、中山路,再向北爬坡三里多的胶州路,才到铁山路德顺和工地。父亲就这样每天早出晚归,为了生计奔忙着。
普通市民市场供应的是苞米面、橡子面(柏罗树籽)、小米、高粱、少量白面和黄豆等,大米是违禁粮。在西岭住时,距后海崖较近,渔船每天都靠岸将打到的海鲜卸下船。我们住的大杂院路北,也是个平民院,门前就有一个专炸新偏口鱼的街摊。呀!每天早晨街面上飘散着那种炸鲜鱼的香味。五岁的我,被这扑鼻的香味馋得光想去摊边玩耍,却不敢向父母要买着吃。我们家每天能维持着苞米饼子、豆腐渣,顿顿有咸菜就不错了。
有时跟父亲去他工作的木匠铺玩耍,赶上樱桃上市季节,爷俩黑天回西岭家时,途经费县路,铁路天桥两边华灯初上。在桥灯照耀下两边大筐小篓中红彤彤的樱桃,格外让人垂涎欲滴,加上小贩们的叫卖声,越加想买。也许是父亲怕我黒天走失,他拉着我的小手更加快了脚步,下桥快步走进大牛房墙外的胡同,奔家而去。
在西岭住了近一年,由于居住条件特差,加上父亲早出晚归太累,我们又迁往青岛鄱阳路棉纱厂南邻一幢小院中。三间平房住着连同房主五户人家,直白地说:就是租了个能遮风挡雨的一个床铺。我家与房东一对老夫妇住东里间,靠北墙搭的床铺,北墙上还有个小后窗户,窗户上有铁丝网,窗外就是纺纱厂。白天纱厂工作时纱机噪声不绝于耳,棉絮不时顺风吹入;堂屋进门对面就是撑着幔帐的一对小俩口的床铺,女的干女招待;西里间是两家挑担叫卖的小摊贩人家。堂屋东西两个锅灶轮流做饭。父亲早起上班的早餐,就是卷张煎饼,沾点酱油,用白水送下。这样的生活又维持了半年多。
1939年我们在鄱阳路往时,我右腿膝盖外侧生了一个疮疖。那个年代缺医少药,全青岛街里就在奉天路和州路顶头有一家“中山医院”,也不是我们平民能进的起的。那个时候哪有卫生所、医疗站、药房啊,就连名都没听说过。我腿生疮流脓出血,久不愈合,也找不到医生看。偶听得一个偏方:用湾里的水洗洗伤口可好转。于是父亲就领我去五号码头附近,在青岛卷烟厂西墙外一个大水湾,去洗涤疮口。经过二次清洗,疮口逐日好转,竟然痊愈。
1940年初,父亲比较要好的一位姓王的潍县老乡(俗号大金牙),因老家有事,便将他经营的小木工作坊转让给我父亲经营。这个所谓的作坊,坐落在西仲家洼最西边一条南北向新民路上,门排号164号。路西一侧是一个不高的小山包,上面有一家做日本木屐的小作坊。距小作房近一里路左右的台东六路最东头,是一小市场,什么打鱼鼓的,说书的,抽签算卦的,煎热糕的,卖凉粉的,炸绿豆丸子的,烀玉米大饼子的,十分热闹,是平民饮食市场较繁华之地。
父亲接手的这个小木工作坊,由三间砖瓦结构的平房构成,其房东是一个名叫柳岛的日本商人。他利用小作坊加工木器家具,由他在铁山路商店销售。父亲接手后,在家乡找了三名本村的木匠同行和他一起做,父亲的大侄子也来跟着父亲学木匠活。母亲自然地成了厨房的大师傅。父亲在作坊的后院搭建了厨房,并连着厨房建了一个带土炕的厦子。一家人有了自由的居住空间,找来的同乡也在作坊的东头打了吊铺睡觉,人多时也在作业的案子上睡。
私塾老师离作坊100多米,有一所名号为仲家洼东岭书屋,老师名叫郭少侯,潍县城里郭宅街人氏。郭老师是一个68岁的老人,不修边幅,一把白花花的过颈长须,身着一件破旧的灰呢子大衣,弓腰驼背,蹒跚地拖着生满连疮的右腿,恰似电影上济公活佛的形象。他耳聪目明,思维敏捷,满腹经纶,是一个教学有方、唯人可亲的好老师。
郭老师教着大、小三十多名学生,他认真负责地对待所教的每位学生,严于施教,讲桌上的戒尺、藤子棍时时不离。我6岁半入塾,郭老师给证的第一课就是《三字经》。从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到“融四岁,能让梨”十几句,念了一天。第二天早晨,合书给他背诵。若能背诵无误,就给书上粘上一小红纸,以示奖励。若背不过,再延一天,若三天背不过,那就要戒尺伺候。也有个别同学小手心被杖打,手心肿胀起来,回家后也不敢流露。
那时,数学课就只学《九九歌》。写仿课时,老师再教“一去二三里……八九十枝花”,并要同学们用毛笔一一书写。两年半私塾,我读完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《庄农日用杂字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千家诗》等经书,从末受过老师的鞭打之疼,幸哉幸哉!郭老师因为我上学点实(认真),从不旷课,按时完成学习任务,特别给我起了个名号,曰“静波”。
学堂趣事我们的书屋在一个半截土墙的小院中,一个开的不大的墙豁口作为院门,无进院门楼,进院便面对坐北朝南的三间通间草房学屋,东面一个小厦子,住着老师和师娘。学屋内周边及中间摆放两排各式破旧的条桌,学生自带坐凳,进门北墙正面,悬挂着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大画像。学生早上第一次进课堂前,首先要在门外向孔夫子深深鞠一躬,然后才能进教室。教室里容纳着年龄大小不等三十多名学生,最大十五岁,我最小六岁半。
学屋西山是一个露天厕所,不分男女只有一个便坑。为了男女学生入厕方便,教室门框上分别挂有“男生”“女生”两个小箭牌,如果有人如厕,则根据自己的性别选择箭牌挂在厕所门外,用这样的方式来界定厕中或男或女,如有人在用厕,不会发生另人再误入之事。
老师根据文化程度高低及学程长短,将学生编成两组。学程长、文化程度高的一组,念《论语》,老师从中选出一名学生称为“大学长”。其余的学生为二组,从中推选出一名学习好、认真负责的学生,叫作“二学堂”。大学长和二学堂两人来管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,如学生的签到出勤、组织打扫卫生、督促作业等事项。正课时间,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,布置不同的学习任务,因人而异,因材施教。有念读的,有背诵的,还有毛笔写仿的,同学们各自为战。
我的同桌齐峰山同学长我四岁,山东莒县人。他家以摊煎饼为生,煎饼炉上常年烤着咸刀鱼鱼头,既香又酥,每次带到学堂就与我共享,作为我们的下饭菜。临桌同学是即墨人,同学们送他外号“即墨地瓜干”。他经堂偷偷地带一小镔铁茶缸,里面装着酱油泡小葱和虾皮子,自己用细铁丝拧了一拃多长的小叉子作为餐具。课间趁着老师不在,偷偷递给我和峰山同学吃,感觉特别有味道,是我们当时的美味零食。这道小吃成了我这一生的保留小菜,这同学之情也让我记忆终生。母亲有时也给我5分钱,买一包五香花生米,揣在兜里带到学堂,与同学们分享。
我刚开始念《孟子》不久,老师右腿上的连疮逐渐恶化起来,行动迟疑不便,疼痛一天比一天厉害。期间,我还为他提着四鼻小磁罐去南山饭市买过羊肉汤,以求滋补病体。当时学生们见他无法正常授课,也就纷纷退学而去。我在九岁那年转入台东六路小学,念起了国语、算术和常识。洋学堂没读几天,因母亲有病,父亲的作坊也不景气,我就辍学回家了。
辍学顽童那是1943年的春天,母亲整天操劳家务,加之给大家做饭等,身体逐渐衰弱下来。因为吃饭时喝了凉水,得了红白痢疾,父亲不但要照顾母亲,还要承担起母亲所有的家务和工作。工友陆续离去,作坊只能勉强支撑。
我辍学后,无所事事,真正成了一个顽童。不时地在门前新民路上滚滚铁环,同小伙伴玩游戏,常玩的有打尖、弹琉璃球、投窝(在地面挖一拳头大的小坑,用光绪年的三块铜钱使糖瓜粘在一起的小铜饼,投向远离十步之遥的小坑,能投入坑中者为赢家)等小游戏。
一次,我用父亲给街里送货用的那辆脚踏车学车时,前轮撞到一块石头上,我摔倒马路中间,头部正倒在路中被雨水冲刷的凹沟中,后面突然冲来一辆轮马车,右车轮从我头边越石而过。在房前闲坐聊天的邻居们眼见此景大惊,高喊“压着孩子啦!别让马车走了!”一拥而上的邻居们首先拉住赶车的老汉,我被人们扶起,手摸头顶发现头没破也不疼,摇摇头对大家说:“不要紧,没压破头。”这时邻居们才放走了马车。邻居们看到的是车轮被我的头颠起,其实是车轮压在我头边的石头上。真是万幸,躲过一场致命的车祸。
(刘爸初稿 刘娟整理)
——本文刊载于2023年《北海道》春季刊